
謝謝你的美好
嚴爵(Yen-j)
2010-04-22 · 華語/流行音樂
從10歲開始寫歌、製作、錄音、編曲、彈奏樂器,嚴爵早已練就十八般武藝,對於一個新人來說,我們讓他首張專輯就自己擔任製作人,或許是一個大膽的決定,卻絕不是一個錯誤的決定。雖然沒經歷過一次完整的製作流程,但靠著適時幫助,他對專業技術理解得非常快。我們找來製作能力全方位的Andrew(朱敬然)來協助他,把一個害羞內斂的年輕人,交給性格熱情外放、工作起來嚴謹細膩的製作人來刺激碰撞,最後的結果是一張豪華的音樂饗宴。第一次進他嚮往的專業錄音室和Andrew見面,嚴爵把帽子壓得低低的,坐在一旁,老半天不說一句話。在他還沒弄懂周遭狀況的之前,沉默是一種安全機制。幸好未來很長,時間總可以找到方式改變局面,如同自認不會唱歌的他把每首歌一唱再唱,編曲一修再修,20個月之後,當他與Andrew的溝通已經變成一個眼神就能互相理解,他的專輯也在推翻與重整中漸漸成形。做唱片的日子,他一天可以寫一首歌,每寫完一首就把專輯的曲目重新排一遍。排的時候仔細分析歌的類型,然後寫下取捨的原因。後來的專輯成品,是大半年加歌減歌排列組合了幾十遍的結果。10歲就赴美留學的他,中文不算頂好,卻很勤於用中文字表達,配合上骨子裡透出來的極致認真,結果就是每次丟給他一個問題,他都寫份萬言書來陳述想法,弄得我們做企劃的都汗顏。他做每件事都有一個邏輯順下來,那種老神在在是彷彿只要他想過的,他都可以掌握。有次他買了一隻手錶,說要戴到三十歲,說屆時應該結婚了,事業有一些成績了,然後才要換一隻新錶。他還清楚計算,自己過去用五年時間把一項樂器練到專業級,那麼未來十年,應該可以再將兩項樂器練到專業級。我想到自己過去十年裡至少丟了三隻錶,想學的東西從來都是半途而廢,一年後的事情我都不敢預測,怎麼有人能把不可控的人生,活得那麼不偏不倚?嚴爵可能真的是可以的。他那種單純專注,無可救藥的偏執,簡直令人羨慕。有陣子讓他做偶像劇《敗犬女王》和《下一站,幸福》的配樂,一般的編曲人,一天做出一首已經算是神速,他卻在一週內給了我二十多首,每首都能用。那段日子只要打電話給他,他聲音都在一種虛無狀態,大概整個靈魂都暫時借給了音樂。聽過很多喜歡音樂的人跟我說,音樂是他人生的全部,可是他們接下來都會開始談論風花雪月吃喝玩樂的其他;但嚴爵很絕對。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聊過別的事情,我得花很多時間研究爵士樂和聽他寄來的DEMO,才有辦法跟他吃一頓飯時可以盡興。一直到後來快發片了,接踵而來的企宣活動使他不再能整天窩在家裡做音樂,難得有一天空檔他一定用來寫歌。他總是在音樂裡調整呼吸。「嚴爵天生就是要用音樂美好這世界。」這是老闆在新聞稿裡下的廣告詞,對我而言卻很是真實。做唱片的時候常常在寫廣告詞,如果有那麼一些時候,那些感動不用思考就自然而然從筆下竄出來,那就是嚴爵的音樂所帶給我們的美好。憑直覺‧相信嚴爵“不知道該從哪裡說起,什麼時候做的決定,我,一個從小沒有唱歌習慣的人竟想當歌手。這一個決定差點鬧起家庭革命但好險沒有,爸爸媽媽姐姐現在都全心全力為我加油。” ----[困在台北]做音樂很快樂,但要讓自己的音樂給很多人聽見,用什麼方式聽見,過程卻總是辛苦。這行業弔詭之處在於,努力與收穫往往不成正比,可一旦踏上了,相信了某些直覺或者宿命,拼命向前只怕是唯一的方法。我們對嚴爵的相信,並不能代表市場對嚴爵的相信。但如果沒有了那份偏執,我們還怕被認真的他給看扁了。背負著醫生家庭的期許,經歷所謂高社會地位、高等教育的成長環境,嚴爵卻一頭栽進不歸路,從名不見經傳開始力爭上游的演藝人生,這梗可能沒什麼新鮮,但講起來依然是血淋淋。許多簽約新人都有過同樣過程,在發片之前的等待中,感覺那上舞台的最後一步,彷彿遙遙無期。嚴爵的父親是南部的婦產科醫師,對於兒子走上音樂路,不捨其實多過於不情願。他曾專程上台北,約我詳聊「娛樂圈」這個他不理解的產業,了解在專輯發行前,「發行單曲」、「巡迴走唱」、「拍照宣傳」各項動作的因由。而當我企圖安撫他,請他「給嚴爵三年闖闖看」時,那位慈和的父親卻回應以堅定的語氣,告訴我說,他希望兒子「選擇了這條路,就好好地走下去,走十年都沒關係。」發行【困在台北】單曲那段時間,預算有限,我們土法煉鋼,讓害羞的嚴爵帶著一架鍵盤、一把吉他,三個月內跑了40場PUB演出,累積臨場經驗。金牛座的完美主義,使他自己吃足了苦頭。一次小小忘詞,就在部落格上懺悔;一兩句talking沒順好,就要沮喪三天。到後來我們根本不必督促他進步,反而擔心他對自己太嚴格。有時演出現場只有三個人來聽,他也是一個人靜靜地彈完了,我們以為他不在乎,好幾天以後才勉強從談話或者文字的蛛絲馬跡裡,看出他當時的DWON。他整個人天生就有一份寧靜感,就像他音樂裡的行雲流水,直率爽脆,卻把細節藏在深處,彷彿只等待有緣人。我曾以為他不會生氣,年輕未必氣盛,可在做單曲時,為了封面跟文案相關事,他終於與我大吵一架。衝突引爆的詳細原因已不可考,只記得那夜之後,嚴爵反而對自己的固執看得透徹。隔天我們約見面時,他站在熙來攘往的台北街頭,眼眶紅紅的,說實在有些壓力了…我忽然驚覺自己忘了他終究還是個孩子。21歲的時候我們還在大學裡呼朋引伴,他卻已經選擇了一條孤獨的道路,從此將跟大多數人不相同。Live House走唱的幾個月裡,有很多事情都不確定,包括我們把發片期一延再延,混音完成的歌還拿出來改內容、重唱,造型也反覆調整;他在這些過程裡從抗拒到理解,從沮喪到接受,才終於找到自己角色的位置。“只是 大家跟我說 大家都勸我說千萬不要這麼做 怕我之後承擔不起後果@4$^!@#$%^& 我 我都聽不懂運氣都差不多 我們 那麼多那麼多後果一切的結果不是我們可以掌握但若你洽我 我暫時不在家喔因為我追尋自由…” -----[追尋]【謝謝你的美好】這張用21年人生醞釀、做了20個月的專輯,是嚴爵送給這個世界的第一份禮物。我們固執地相信,那音樂帶給我們的快樂,是也可以帶給其他人一些什麼的。也許信仰終究不是真理,沒有人知道嚴爵能走到哪裡,可在這岔路無數的年代裡,總還是要有人去找一條康莊大道吧。這幾天在練團室,看嚴爵彩排23日在The Wall的個人首場full band演出,他彈keyboard大聲唱著歌,跟幾位國際級頂尖的樂手老師飆樂器,面無懼色,只有發自內心的悠遊自得。想著專輯發行之後,這男孩的人生將從此不同,他將成為公眾人物,音樂將成為類似使命一樣的東西,我們只能有點心虛地期望,這一趟路燈紅酒綠,我們都沒有做錯什麼。我們都只是在音樂中追尋,人生裡那難覓的,栩栩如生的美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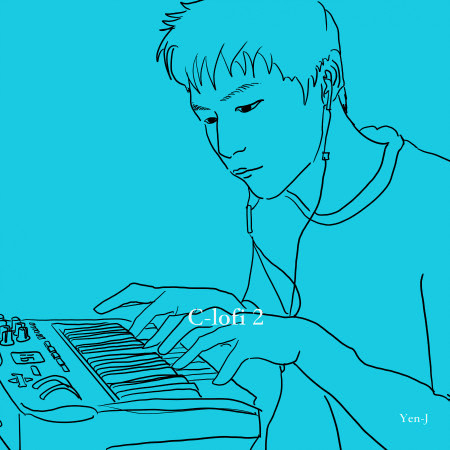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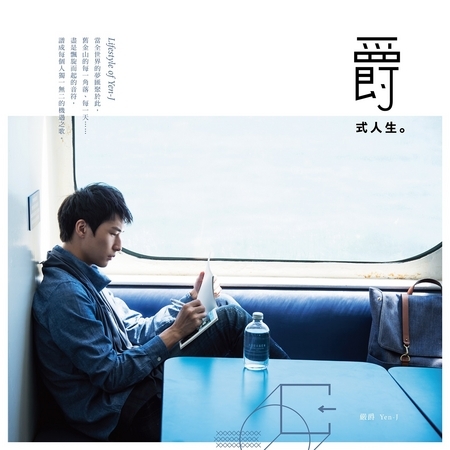



![[爵隊製作實驗室] project 1-1 EARTH](https://lineimg.omusic.com.tw/img/album/1034897.jpg?v=20200319215604)